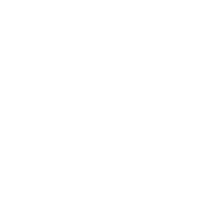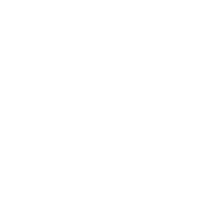儒家“德行伦理”的道德评判原则及其现代意义
 发布日期:2025-12-03
发布日期:2025-12-03  浏览量:2267
浏览量:2267
前言
儒家伦理的特征是多元的,这不仅表现在不同的学派之间,也表现在某些单一的儒学理论中。例如,叶适、陈亮的伦理学偏于强调事功或后果,而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伦理学则偏重内在德性;回到先秦儒家,人们会发现,至少孔子的儒学并不完全是事功主义的、德性主义的或者其他主义的,而仿佛是它们之间的某种杂糅状态。陈来、陈继红等学者将此种伦理形态称之为“德行伦理”。德行伦理似乎是一种带有较强习俗遗留、原理性不强或带有杂糅性质的伦理学。不过,在本文看来,这正是儒家德行伦理的特色之处,即它在规则伦理、德性伦理、后果伦理等伦理形态之间取了一个中道,因而可以避免各种伦理形态的偏失。这样一种中道的伦理形态不是各种伦理类型的简单杂糅,而是有其一以贯之的理论根据的。本文将对儒家德行伦理背后的原理进行挖掘和发挥,并在此基础上呈现一种以仁爱情感为本源,以“缘情用理”为根本方法,集德行评判、德性评判、德操评判为一体的儒家德行伦理理论,或者说儒家情理伦理理论,这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儒家德行伦理及其现代意义的认识。
一、德行伦理“称行为德”的特质
德行伦理并不是一种被当前学界广泛接受的伦理学形态,因此,对德行伦理的特点做清晰的论述是必要的。关于德行伦理的主要特征,陈来、陈继红等学者曾做过详细的辨析,根据他们的研究,德行伦理的主要特点如下:
德行伦理中的“德”不仅包含人的内在品德,而且包含人的行为和行为规则。德行伦理致力于道德心理与行为规则的统一,而不是将其中一个方面作为伦理学的绝对的中心。
陈来和陈继红在儒家德行伦理的认识上也有一些不同。比如,按照陈来的观点,并非全部的儒家伦理都属德行伦理,他认为孔子的伦理学是德行论,因为孔子所讲的仁、孝等德目延续了西周以来的用法,很多时候都是指人的行为规范,而到了孟子那里,虽然德行的用法还存在,但“传统的主要德目在孟子思想中已经从德行渐渐变为德性”。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孟子“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以及“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的主张。这也就是说,孟子的思想基本是德性论,因而不属于德行伦理的范畴了。陈继红则认为整个儒家伦理学传统都属德行论。因为她发现儒家长期存在将德目作为行为原则理解和使用的情况,如“仁,是行之美名”“行之而人情宜之者,义也”“人伦日用,其物也;曰仁,曰义,曰礼,其则也”,等等。于是她将儒学史上偏于内在品质或偏于行为规则的伦理学说看作德行伦理的两种展开方式,而不是两种形态的伦理学。
在对儒家伦理形态的归类问题上,由于不同儒家学派的理论观点差别较大,这里倾向于赞成陈来的态度,即对它们做出不同伦理形态归属的区分。即,思孟学派以及继承思孟学派的宋明理学,或者说心性儒学,不属于德行伦理,而是属于德性伦理。原因在于,这些学说的理论核心的确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虽然它们也会从行为原则的方面去阐释“德”,或者说它们所言之“德”包含“行”,但行不是第一位的。正如“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之“行”,其在根本上是内在之“德”的外在施行、践行。虽然在宋明理学中,“德”有行为规则的内涵,但此行为规则在根本上属于天命下贯于人的本心、本性,内在品质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心性儒学家虽然主张内在道德心理与外在规范的统一,可是这种统一性得以成立的关键,是外在规范必须合乎人的本心、本性之理,因此内外统一性的重视不能掩盖内在德性的第一性地位。由此可见,要想对德行伦理做出更为清晰的界定,需要对上文总结的特征做出进一步的限定,即:德行伦理不能是以内在品质作为德的第一规定,道德心理与行为规则的统一不能是以道德心理为主导。
(然而,反过来以行为规则为第一规定、为主导可以吗?不可以。这样的话,德行伦理又成为地地道道的规范伦理了。那么,德行伦理的特质究竟在哪里?它是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中间样态吗?这种中间样态具有理论的一贯性吗?或者它只是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充满矛盾的杂糅状态?不可否认,德行伦理在形态上的确类似于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一种中间样态。有学者称儒家伦理为“示范”伦理。“示范”这一概念非常形象地表明了儒家德目似指导性原则而又不具普遍约束力的特点,因为能够做“示范”的,在根本上只能是一种行为或行为方式,不是内在的品质和普遍性的原则。
“示范”伦理的概念提醒我们注意行为与行为规则的区分,将这种区分纳入德行伦理学,我们或许会发现在德行伦理学中行为与行为规则之间亦存在第一性和第二性问题。即,德行伦理学只有以行为为第一性,行为规则为第二性,才能保证它不是规范伦理学。同样,以行为为第一性,内在品质为第二性,才能保证它不是德性伦理学。通过这种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划分,我们也能认可在广义上行为、内在品质、外在规则均被称为“德”。所以,德行伦理学的德目可分成三类,一类是行为之德,一类是规则之德,一类是内心之德。在理想状态下,行为之德是基础,规则之德是行为之德的原则化、抽象化,内心之德是行为之德的内化,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规则之德与内心之德之间也会发生相互的同化性影响。但按照德行伦理的理想规定,道德心理与外在规则的统一,不是内心之德与规则之德两者间的调和损益问题,而是以行为之德为标准去平衡内心之德与规则之德。这样的话,德行伦理虽类似于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中间形态,却着实不是两者的杂糅,而是可能拥有自己的融贯主张的。不过要将此种可能性落实,还必须为行为何以成德找到一种不属于内在品质和外在规则的根据。
依照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人性论,人固然有其自然之性,但人性也会通过“习”而发生变化,由于孔子本人并不是先天德性论者,因此在孔子那里,德是通过“习”而养成的。基于王夫之关于“习与性成”的诠释,黄玉顺指出孔子这里的“习”,指的就是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如此,德也就是日常生活实践的一种积淀,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实践中积淀的一种习惯性行为。习惯性行为的养成包含着主体情感、理智的参与,也包含着外在规范、知识的学习,整个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孔子所赞成的良好行为之养成,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外在规范的内化或者内在品质的践履,而是一种基于仁爱情感关照、理智思考、后果考量而适度接受和改变外在知识与规范的积淀过程。只有这样,新的习惯性行为的养成才具有德行生成的意义,德行才具有不断的示范效应。在孔子哲学中,我们当然可以说“仁”是养成良好习惯性行为中最具有源泉意义的因素,但最本源的“仁”绝不是人们通俗理解的已经现成化的道德情感或自然的血缘亲情,它尚不是一种德行和德性,而是在行为实践中人与外在世界相碰撞中产生的不麻木、敏锐的情感反应,正是这种情感反应为理智提供源初的思考方向,将人的内在需求与生活境况结合在一起,从而促成了具有崭新意义之行为的产生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宋儒喜用中医手足痿痹为不仁的说法来诠释仁,这是把握到了仁之源初的情感不麻木状态的内涵,但他们在理论上将其赋予道德意义并提升到先天的高度,这便违背了孔子的原意。
所以,就仁而言,人自然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原本不是德性,要首先经过一定生活经验积淀成回避观看弑杀牛羊的习惯性行为——德行,然后再内化为持续性的内在的仁爱性情——德性,以及抽象化为不乱杀生、仁民爱物的仁爱规范。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若以非品德化之源初的仁爱为判断基础,辅之以理智的思考,对知识、后果、现有的规范做出综合的分析,这便成为评判习惯性行为之好坏的标准和养成良好的习惯性行为的基础。此方法可以称之为“缘情用理”的方法,由此方法判定的“行为”标准既不是纯粹内在的品质,也不是现成既有的行为规则,因而足以为上述三德区分的德行伦理提供支持。
以上分析显然是对孔子思想的引申,孔子本人并没有对行为之德、内心之德、规则之德做明确的区分,更没有对仁的内涵做上述区分和分析。但通过上述引申性的探讨,我们能够为德行伦理作为一种区别于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的理论形态找到更充分的理据。因而可以对德行伦理的特点做更为精准的概括:
1.德行伦理是"称行为德”——以某一类行为为德——的伦理学,它以前德性和前道德规范的行为之德为根本衍生出内心品德和行为规则。
2.德行伦理注重道德心理与行为规则之间的调适,行为之德是调适其他两者的标准和媒介。
二、“德行”“德性”“德操”的区分
以上论述了德行伦理的特质,这里将详细讨论德行伦理在道德评价之“品德”评价中的应用。
必须指出,品德评价与善恶评价(道德是非的评价)是不同的,因为德更注重习惯、习性的养成,一般情况下不能通过一个偶然的、片段性的行为来做评判,而是需要通过个体一系列的行为来做评判。但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如此。相对而言,判断一个人无德,要比判断这个人有德更容易,因为一个人一旦做出了一次特别残忍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判断他缺乏仁性,或者说缺乏仁的德性。然而,我们却很难通过某人的一次善良行为,就说这个人有仁德。而且行为善恶的判断与是否有“德”的判断也是可分离的,一个仁德极为欠缺的人也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做一次善事。因此我们不能把是否有德的判断与行为是否善恶的判断等同起来。
还要指出,德行伦理学关于是否有德的判断相对比较复杂,德行伦理所认可的德有三种,即行为之德、内心之德和规则之德,那么对践行三种德的行为亦可做三种判断,即是否有德行、是否有德性和是否有德操(操有操守义,这里用来指称对行为规则的持守)。德行伦理学在面对具体的行为时,将根据上述三种情况进行判断。
例如,孔子极少许人以仁德,但面对不守臣节却能匡扶社稷、挽救千万百姓于死难的管仲,孔子却评价他说“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这是很高的评价,然而管仲似乎又不值得这样的评价,因为孔子还说过“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于是如何解释孔子的评价便成了难题。朱子对此作了一种变通的解释,他说:“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这实际是将仁的内在品德与实际的行为效果做了区分。他承认管仲行为的仁德效果,在根本上却不承认管仲有仁德。因为朱子是一个德性论者,他只从内在品质上判断是否有德,管仲有仁之功,却不能说他有仁德。而无仁德的人,却能有仁之功,这似乎也很尴尬。李泽厚则一反朱子的观点,认为孔子就是“从为民造福的巨大功业出发来肯定管仲的,正如将‘薄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放在‘仁’之上一样”。李泽厚之所以有此观点,主要是因为他是从效果的视角来认识孔子之评价的,而将“仁”德评价完全效果化,就难以对管仲不守规范的一面给予适当的评价。依照上文德行伦理学的判断标准,管仲的行为及其效果确实是合乎仁之德行的,他并未做残忍不道之事,根据已有的资料,我们也无法洞察或推测他有仁爱的性情,故没法判断他是否有德性,但他违背臣子应有的行为规范,确实是无德操。因此,我们说管仲有德行,无德操,不知其德性。这既许之以仁德又没有许之以全部的仁德,如此便与孔子“如其仁”和“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的评价相一致了。
假如我们能够通过某些资料发现,原来管仲的一切行为实出于卑鄙恶劣之心,其最终目的只是为了玩弄权术、荼毒百姓,其种种善行不过是其邪恶目的实现之初步的手段,然而纵观其一生,又确实没有任何施展恶行的机会。那么,我们便可以判断说管仲实无德性,而确有德行,然后再根据其遵守规范的情况判断其是否有德操。
当然德性不一定要通过“动机”来评判,德性品质可以是一种修养的圆熟状态,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指的就是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主体没有遵守规范的动机,即不需要内心的克制和持守,却能不勉而行,从容中道。从低处看,这或许只是道德规范熟稔于心的状态;往高处说,也可以将其提升到道德本体境界:“至于一疵不存、万理明尽之后,则其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心所欲,莫非至理。盖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义,声为律而身为度矣。”程颢对此种境界亦有清晰的论述:“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此种“无心”之境界,即冯友兰所谓“不是出于一种特别有意的选择,亦不需要一种努力”的“天地境界”。在儒家传统中,这种境界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圣人在此境界中的一切行为皆属“无心”之行,但我们不能说圣人是无德性的,圣人不仅有德性,而且还有德行与德操。
圣人兼具德行、德性、德操,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此种理想状态的实现,不仅要求主体人格是理想的人格,而且亦要求主体所生存之世界是理想的世界,即在此世界中,内心之德、行为之德与规则之德这三类德目能够协调一致。按照宋明理学德性论的观点,圣人的判断标准只在内心之德的圆满,其身处规则不正义的社会中,所行虽不与行为规则合,亦不妨害其品德的圆满。但在德行伦理看来,于无道世界之中,绝无品德圆满的圣人,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普遍的行为规则,人们可以在此社会中践履德行、涵养德性,却不可能有德操。所以,在德行伦理学的评判标准中,有德者易出,而圣者难成。欲成大圣,必须本着其在生活世界中体贴积淀之德行,重塑社会之德性标准与德操标准,推动社会从不正义到正义,从据乱世到太平世,如此方可。可见,德行伦理学的圣人标准是从宋明理学德性修养的圣人返回到了先秦“尽伦”且“尽制”、圣王合一的传统中了。当然,圣人不必一定做君主意义上的王,推动理想社会实现的人也不一定是君主意义上的王,“王”强调的是推动社会不断朝着理想进步的责任和实践。在此意义上,德行伦理的品德要求要比德性伦理更加直接地肯定社会中的善行。加之德行伦理能够承认“德行之行”的品德价值,因而更容易接引和鼓励人们走上德行践履之路。
德性伦理当然也要求内在品德的外在实践,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明确主张“行是知之成”,这是说,倘若缺乏行的环节,便不能算是良知圆满的呈现。在宋明理学中,阳明学已算是最能鼓动实践的学说了,但在德性伦理的框架下,“知是行的主意”,必先于“知”(良知、德性)有所领会和造诣,然后才可能有真正的行。可是这先行的领会和造诣本身所需要的努力,就足以牢笼人的手脚了。当然,阳明学中又有“良知自然”“良知现成”的一派,这一派主张良知现成存在、自然呈现,于是取消了领会和修养的需要,真真是用全力于行,但因为缺乏“主意”的领会,即缺乏实际德性的涵养,结果只好“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这实在有盲行的一面。另一面,我们也不能说这些阳明后学的思想完全没有“主意”,它们的主意是一片赤诚情意、拳拳“赤子之心”、自然无伪的“童心”,这实际上有思想解放和启蒙的意义,然而这些不假修饰的“主意”及其实践,实际已经脱离了德性伦理的范畴,是自然人性的彰显,不是道德德性的践履。所以,我们看待阳明学,一定要审清它内蕴的保守德性伦理与颠覆德性伦理的两面性。嵇文甫说,“阳明学派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一方面把道学发展到极端,同时却又把道学送终”,此乃卓见。因此,就作为德性伦理的阳明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而言,“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之社会现象的出现不能说与其毫不相关。明清之际儒家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正是基于对宋明德性伦理之弊端的反思。若德性伦理真能有效激发个体参与社会实践和改造社会的行动,则明清之际以后儒家“走出理学”的发展路向,岂不是无端肇事么!
三、道德善恶(是非)的评价标准
品德评价通常需要综合一个人一系列的行为、性情进行评价,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对某个单一的行为作出评价,这个时候虽有可能涉及品德评价,但更多可能涉及的是善恶评价,或者说道德是非的评价。德行伦理要想成为一种完善的伦理学,不能不对善恶评价的方法和标准作出说明。
在判定品德的时候,我们根据的是“德”的类别而做分别的判定,在善恶判断的时候,我们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在三种德不一致的情况下(现实中三者很少完全一致),三种标准判定的结果是不一致的,而善恶判断要求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么,如何在德行伦理的视域中探求确定的善恶标准呢?
须知,品德判断与善恶判断固然不同,其不同不在于行为的性质,而在于行为是否是习惯的或持续的、一系列的。就此而言,德行伦理判定品德的根本标准是可以用来评判行为善恶的。在德行伦理中,最根本的品德判定标准是德行的判定标准,因此德行的判定标准亦可以作为行为善恶的根本判定标准。德行的判定标准是比较复杂的,需要运用情感、理智综合知识、环境等多种因素,不是一种方便、明确的判断方法,是故我们必须通过一种折中的方式使之简化。其实,在行为之德与规则之德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体现规则之德的规则来评判善恶,在此意义上,行为之德或行为之德的评判标准便成为行为规则是否正义的优先判定标准。只有当行为之德与规则之德不一致时,我们才需要返回来用行为之德的判定标准进行裁决。内心之德与规则之德是同一层面的品德,但内心之德不是具体的规范,在判定善恶方面具有模糊性,因此我们不选择将内心之德和内心的动机作为判定善恶的优先标准。这样的话,德行伦理的善恶评判标准可总结为:
1.如果现行行为规则和德性是正当(合乎德行)的,行为的善恶由行为规则和德性判定,前者优先。
2.如果现行行为规则和德性是不正当(违背德行)的,行为的善恶由德行判定根据(缘情用理)判定。
上述善恶评判规则尚需做进一步解释。首先,德行伦理优先运用行为规则进行善恶判定,当规则条款不适用时,人们可以启用第二条款,然而为了尽可能地保证善恶判定的准确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应该尽快运用德行标准修订行为规则,从而尽可能地保证行为规则判定在善恶判定中的应用。这虽与规范伦理具有相近性,但毕竟在判定的根本标准上不是规范的,因而不同于规范伦理学。
其次,运用德行标准判定行为规则之正当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第一种方式是根据德行,德行不同于德性(良心),它具有更为清晰的行为范导性,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正当行为的标本。在现有行为规范需要变革的时代,总会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德行,这些德行必然是与原有行为规则不同的,因此可以参照德行修改现行行为规则。第二种方式是根据德行的评判标准对现有行为规则进行修订,这适用于旧德行不适用、新“德行”尚未形成的情况。事实上,总有一些普遍性的德行是在任何社会中都适用的,比如“仁者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样的常德,它们为任何种类的人类社会的基本行为规则奠定了基础。不过,这里主要考虑的是需要变化的德行。德行的评判标准是比较复杂的,要根据人们在新处境中的本真生活领会或情感感受,引导理智和认知,综合现有知识和环境而做出判决。这其实就是上文讲到的“缘情用理”的方法。
不可否认,缘情用理的评价标准并不是一个特别精确的标准,因此判断结果的达成确实要综合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情理”。但这种根源上的模糊性在道德情感主义传统中也并非不存在。比如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合宜的善恶评判需要“公正的旁观者”的赞成或不赞成的情感来决断,而个体要想将私人的情感提升达到或接近“公正的旁观者”的水平,需要一个戴震式“以情絜情”的过程。此过程如何才算是达到了公正合宜的标准,同样不容易讲清楚。“缘情用理”其实不过是在此过程中明确地加入了理智的因素而已。这并不是说情与理两者始终是割裂的,两者通过融合最终可以积淀为公众的“情理”,李泽厚称之为“情理结构”,并可以通过理智化语言和情感感受表达出来。由此,德行伦理本质上不过是情理伦理而已。只不过这里的“情理”不是指情感的先天原理,而是“缘情用理”的心灵活动。
最后,德性不被用作优先性条款。这正是德行伦理与德性伦理的不同之处。根据德性伦理,无德性的行为不可能是善的,特别是怀有恶意却导致良好结果的行为不可能是善的。一个想要杀人却阴差阳错挽救了所要弑杀对象的行为怎么能是善的呢?按照孟子的标准,此行为不基于恻隐之心;按照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家斯洛特的标准,此行为并非出于移情性的关心;故此行为不是善的。难道我们要将偶然导致良好结果的行为称为善的吗?我们知道这种不基于动机而基于后果的善恶判断在德性伦理学家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在效果主义伦理学那里是可能的,在德行伦理学中也是可能的,因为后两者善恶判断的根本不是内在动机。德行伦理与效果伦理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从根本上来看,效果伦理的判断标准是行为的后果,而德行伦理的判断标准是某种行为模式。根据德行伦理,有时候后果不好,但合乎道德行为模式的行为亦可以被评价为善的。这是德行伦理与效果伦理的不同。
当德行伦理宣称一种无善良的内在品质和动机的行为可以为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同德性伦理一样不承认行为主体是有德性的,同时,由于该行为很可能只是一次偶然的行为,我们无法判断行为主体做出此类行为的连续性或习惯性,因此德行伦理也不承认行为主体必然拥有德行和德操。承认行为的善,并不代表承认行为主体有品德。这种品德判断与善恶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的可分离性,是德行伦理的一大特点和优势,而这是德性伦理所不具备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在儒学史上朱熹和陈亮之间发生过著名的“王霸义利之争”。从制度规范制定的视角来看,朱熹认为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人物,虽然其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不算太差,但他们的初心是为了自家一姓的私利,因而他们所制定的制度、政策离“王道”相差甚远;而陈亮则认为,“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无常废”,既然制度和政策的效果是好的,那么王道必蕴含在其中。这个例子反映的是,德性伦理学家特别看重政策制定者的德性,并将其看作判定制度规范正义、优劣与否的标准,这本质上是“由内圣而外王”这一思维逻辑的体现,对政策制定者的素质要求过高,对善政、善法本身的评价有失公允。陈亮的思想带有较强的效果伦理的意味,但从德行伦理的视角来看,他的评价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被认可的。
四、结语
通过对德行伦理的特质及其如何进行品德评判和善恶评判的阐述,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德行伦理以行为为中心对行为主体、行为本身、行为规则的分别评判和对品德、善恶的分别评判所具有的优势。相比德行伦理,传统心性儒学之德性伦理将内在德性和动机作为道德评判的核心,这不利于认可和激励改良社会的行为实践的道德价值;对制度和政策制定者过高的德性要求,不利于对善政和善法本身做出公允的评价。现代社会的治理基础是法律和制度,因而在生活中,人们行为的合规范性和范导性会被优先关注和评价,因此,对于现代社会特别是亟需道德规范建设的当下中国来说,德性伦理更适宜作为辅助性的伦理学被推广。如果说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需要加强道德主体的品德塑造,那么在内在品质、行为本身和行为规则三者的调和方面,以情感为本源、以“缘情用理”为根本方法的德行伦理(“情理”伦理)不失为一种更优的选择。
(作者:李海超,男,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本文刊载于《伦理研究》(第九辑)
上一篇 : 以法弘德:传统道德资源创造性转化的一种实践路径
下一篇:《中庸》“柔远人”:儒家的“他者”交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