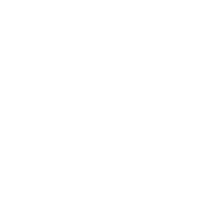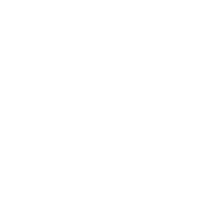《中庸》“柔远人”:儒家的“他者”交往之道
 发布日期:2025-12-03
发布日期:2025-12-03  浏览量:2315
浏览量:2315
前言
“柔远人”是儒家“中庸之道”在治国方略中的具体践行,它所揭示的是儒家对“他者”的认识与转变影响着儒家伦理符号、政治原则的形塑,这一过程也折射了儒家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认识及其转变。如果离开中庸的政治意义与初衷,是很难把握孔子的中庸思想的,作为治国方略的“柔远人”为深入儒家中庸思想的理解提供了有效的路径。本文试图在整个古代中国思想的视野中理解《中庸》,同时也通过《中庸》“柔远人”来理解儒家“他者”的交往之道如何展开、如何影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
一、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庸》及其“柔远人”
在春秋末年的变革中,面临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孔子提出了中庸思想。他认为社会矛盾重重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为了私欲的满足无所不用其极,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中庸思想的提出则为人们在日用伦常、出处进退、视听言动及修身养性中打开文化的生命。将个体生命通过文修化育自己与他人,从而参赞万物。“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在先秦儒家典籍中这是最早关于“中庸”的记载。有意思的是,在《论语》中仅此一见,唯《中庸》记录了孔子对“中庸”的六处论述,孟荀也没有直接的描述。然而,中庸思想却与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紧密关联乃至影响整体中华文化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史记·孔子世家》言《中庸》为子思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与道心杂于方寸之间,唯“中庸”贯通道心人心,参赞化育。因此,《中庸》多被理解为儒家传续道统的典籍,它承载了孔门心法传授。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七略》(即今传《汉书·艺文志》)《中庸》与《大学》一同被归于《小戴礼记》,颇为历代学者所重。自汉郑康成《礼记正义》疏证始,唐孔颖达、宋朱熹都对《中庸》进行了注疏考据,明清顾炎武、戴震均有专门的训诂辑录。近代以来康有为、刘师培等注家都专注于中庸辞章考辨,古往今来注疏不辍足见《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庸》历史地位的确立与朱熹将它纳入“四书”有直接的关联,他花费毕生精力为《论语》《孟子》集注,为《大学》《中庸》章句辩章学术阐发意蕴。使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经学理学化的典范之作。随着《四书章句集注》被列入学宫,元时更成为科举取士必修科目。这一制度被明、清所继承,逐渐演变为八股取士,自此,“四书”成为中国古代士人必读经典,其影响力超过“五经”。“四书”中的《中庸》其序在《孟子》之后,历来被视为儒家修身之学的纲领性经典,这样的历史转变一方面反映出历代大儒对儒家道统的重视,另一方面则彰显了“中庸”思想与中国文化精神持久幽深的关联。
《中庸》从形而上的本体论意义为中国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作为全书的总纲领,乃至儒学总纲领的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与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文本上呼应子思阐发中庸与天命(天道)的关系。中庸的本质在于命、性、道、教四者之间的贯通,正如学者陈赟所言“通过命—性—道—教的文化境域,中庸将上下通达的主题引入到广义的文化的创造与看护过程,而不是限定在个体生命的内在性之中,从而展开了一种‘合内外’的生活的可能性……因而,对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世界的接纳,构成了中庸之道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中庸之道所揭示的是从《尚书》到《论语》再到《中庸》《孟子》一脉相承的道统谱系。这一历史悠远的道统谱系构成了“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成其为是的基底。人们在理解古代“中国”概念时通常指向作为文化符号体系与思想形态的中国。这是因为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只有“天下”场域的“中国”而没有“国家”场域的“中国”。“天下”思想直观地反映了中国人对世界的原初认识,在这种认识之上建立人与“天”的关联,由此拓展到人与人之间、个体与族群、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中庸》不仅在形上意义上贯通天道与人道,而且从人道出发提出了人之为人的秩序(教),儒家修齐治平之旨囊括其中。儒家“八条目”在这里被表述为“九经”: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目,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第二十章)
显而易见,“九经”是在修身—治人—治天下的框架之下所制定的基本举措,相较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而言,“九经”更多地指向了天下国家的治理,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同时,《中庸》一反往常“天意”作为政治唯一合法性的表诠,而试图凸显人的主体性。其中包括人君通过自身修养的臻善所获得“治人”与“治天下”的主体性;另则,“九经”包含了对他者的重视,寻求“民意”的正当性而通达内外一致的“中和”。也正如此,“九经”把治天下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政治方略,“教“的内容进而扩充,内仁而外礼,这与孔子内圣外王的思想一以贯之。孔子向来持“政者正也”的主张,认定政治之主要目的乃是化人,政治与教育同功,而修身是一切之本。“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与《孔子家语·王言解》中“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布诸天下四方而不怨,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都表达了孔子素来以文德怀远人的德治主张与推行王道的政治立场,《中庸》倡导“和者天下之达道也”,治国“九经”把天道、人道、政道具体化,“柔远人”正是在修身—治人—治天下的逻辑框架下展开,怀远人以致“和”以达道。“柔”的态度与主张彰显了中庸执两用中之道,不偏不倚善于变通。
可以说,《中庸》总体上赓续了孔子的政治原则与目标,在家国同构的儒家伦理中,将“治天下”层层推展,上至大臣下至庶民百工,近之修己远及诸侯乃至四方之人。因此,经由中庸通向中国思想谱系来理解儒家文化世界与文化生命,经由“柔远人”来探讨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及其儒家“他者”的交往之道,无疑打开了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与历史逻辑的可能性。
二、“柔远人”:中庸之道的远近之维
在治天下国家“九经”的几个举措中,“柔远人”“怀诸侯”在伦理秩序中处于末端。如果依照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理论来解释,“柔远人”处于“同心圆”结构中的次外围。君子处于“同心圆”的中心,依次向贤能之人、亲人、大臣、群臣、庶民、百工层层外推,远人、诸侯排列其后。但是在这个序列中,并没有将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排在首位,而是把贤者放在离“同心圆”最近的位置。由此可见《中庸》对“德性”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出从君主自身到百工此七者是“修身、齐家、治国”的范畴,而“远人”“诸侯”则转向“平天下”的视域。差序格局注重“推己及人”的过程,“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也把五伦作为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费孝通先生既强调五伦在传统社会中的等级差序,又以现代的眼光质疑了鬼神、君臣、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怎能和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对地位相提并论。换言之,他所强调的是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交往网络中所构成的纲纪(伦常)。倘若完全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解释则遮蔽了《中庸》对“德性”的重视,原因在于《中庸》的九个维度中贤者被放在亲属的序列之前。因此,采用差序格局来审视《中庸》可以看到儒家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以及社会结构特征。但中庸“九经”的具体所指、能指,还需回到《中庸》自身。正如赵汀阳所驳斥的那样,“由家庭伦理推不出社会伦理,由爱人推不出爱他人,这是儒家的致命困难”。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建立在两种坚定的基础上,其一是他虚构了一种“陌生人理论”,并从哲学的角度认为陌生人才是典型的他者。陌生人理论否定了儒家“情感本体”的作用,并且否定了儒家的“情感”在中国社会结构“同心圆”当中是可推导的。显然,对儒家“情感本体”的不同理解也构成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差异对待,情感本体则在对“他者”的关照中得以彰显。
在《中庸》“九经”中,“柔远人”集中反映了儒家“他者”之道,而在历代注疏中也颇有争议,对“远人“的贴切阐释可以更好地进入儒家关于“他者”的基本立场以及深入“治国”走向“平天下”政治追求的理解。在原始儒家经典中“远人”有不同的注释,既有专注空间间隔的注疏,亦有人事权力分疏的注解。《尚书·舜典》“柔远能迩,惇德允元”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常用语,柔者,持安也。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今文尚书考证》中提到汉代“柔”多作“渘”,近者各以善近。直至王阳明在御守西南夷时“柔”亦秉持古人持安之义。“夫柔远人而抚夷狄,谓之柔与抚者,岂专恃兵甲之剩,威力之强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能通天下之志。”“柔”在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中始终昭示着与武力相对的安抚之术,劝和而不讨好,非攻而善和。“远人”则在古典文献中随着古人对疆域认识的拓展而丰富。上文所引《中庸》“九经”之“远人”在《荀子》那里意为与本邦国子弟相对应的其他诸侯国。“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荀子·君道第十二》)《礼记正义》中,郑玄注:“远人蕃属国之诸侯也。”孔颖达疏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远谓番国之诸侯,四方则蕃国也。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怀安抚也,君若安抚怀之则诸侯服从,兵强士广故天下畏之。”在《礼记正义》注疏中“远人”等同于诸侯。但是,从古汉语对仗的书写来看,《中庸》“九经”所指涉的“远人”并非简单地等同于诸侯。在前述所引“九经”的后文“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推论。从这个意义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柔远人”的注解更符合子思在《中庸》中的逻辑展开。朱子将以上引文“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注为:“柔远人,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途,故四方归。怀诸侯则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矣,故天下畏之。”在朱熹的注释中,远人即是远游四方的宾旅。所谓“宾旅”,明代王夫之作了笺解:“宾以诸侯大夫之来觐问者言之,旅则他国之使修好于邻而假道者。又如失位之寓公,与出亡之羁臣,皆旅也。唯其然,故须‘嘉善而矜不能。’”因此,无论从古汉语的对仗、互文见义等原则来看,还是《中庸》上下文的语义关联衔接,“远人”并非直接或者仅仅等同于诸侯这是可以明确的。王阳明在《绥柔流贼》中所言“夫柔远人而抚夷狄”的语境中“远人”是指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显而易见,“远人”的意涵在历代儒学大家及其注疏者视域中愈发宽泛,这与中华民族疆域的拓展不无关系。今人史学家陈柱在《中庸注参》中亦将中庸“九经”之“柔远人”与“怀诸侯”相区分但认为两者相辅相成。也就是说,《中庸》之“远人”为中华文化打开了极有弹性的思维空间,综括历代注疏,在《中庸》的语境中,“远人”更趋向于指“诸夏”以外的四方之民,柔远人,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其涂,故四方归。同时,可以根据《孔子家语》等儒家典籍中把夷狄视为宾客以及古代汉语中“互文”的特殊修辞,有理由认为“远人”包含着夷蛮戎狄四方之民,“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言语不合,莫不来宾”。(《孔子家语·王言解》)
从“柔远人”的注解中不难发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中,先秦儒家的民族观(夷夏观)隐含其中。这也是《中庸》“九经”相比《大学》“八条目”进一步深化了儒家的“天下”思想。“远人”进入公共空间的讨论所涉及的空间视域更广,不限于邦国领地,而是渗透到四方之民的空间延展,正符合孔子和而不同、一视同仁的待人之道,它所指向的是儒家对“他者”主体性的重视。《中庸》第十三章所引“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是关乎人的存在而彰显的,须臾不可离乎人。这里的“人”同时包含着自身与他者,君子之道展开在与他者的关联之中,由此而言,“柔远人”既是方法论的精神原则又是道之具体践行。值得指出的是,朱子对“远人”的注解更多的是依照具体情境而论,而非给予固定的解释。比如,在《论语》集注中,“远人”指鲁的附属国颛臾。《论语·季氏》:“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朱熹注,“远人,谓颛臾。”“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何以伐为?”将朱熹两处的不同注解进行对比,意在强调《中庸》“柔远人”的既是作为方法论的精神原则又是功夫论的具体实践,而非拘泥于辞藻章句的训诂。作为方法论的柔远人所体现的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彰显——对“他者”的重视,作为功夫论的柔远人表明君子修身的目的与践行。这样的研判是建立在“远人”在先秦儒家经典中从特指颛顼诸侯国到四方之民的泛指,从这个角度来说“远人”的外延是随着中华民族演进的历史而言的。随着对地域范围认识的扩展,“远人”的范围随之外扩,而“柔”的意涵自《尚书》“柔者,持安也”从作为安抚、怀柔之义到平等和顺的待人之道,表明儒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既非以武力攻伐,也非一味讨好,而是建立一种对外交往的道德价值体系。此乃“中庸”之“执两用中”的体现。也就是无论是对待诸侯国颛顼还是四方之民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儒家一以贯之践行中庸之道,“柔远人”亦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中获得更为丰富的意义。
由于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实体,一切社会关系均由个体的人层层拓展、相互关联形成严密的人际网格。“柔远人”作为先秦儒家夷夏观的方略,亦通过君主修己并由一圈圈人际格局“推”至开来。“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远人只有得到安抚才能保证四方之民归顺,给予诸侯怀柔政策天下才得以长治久安。在没有实体民族国家的情况下,四方之民归顺的是统治者,那么,统治者的“德性”则是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君王只有修其身,施行仁义方得天下之民的拥戴。在古代中国“天下”思想的影响下,“四夷”被纳入“天下”体系,并且可以经由礼乐教化转而为“华夏”。《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尚书正义》对“华夏”的解释是“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中国”则是相对于“四夷”对应的概念,早在《诗经·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鲁颂》“至于海邦,淮夷来同”就有两者的区分。在先秦儒家“天下”思想中,从区位与政治观念上以“中国”为核心,才会出现“远人”“四方”“九州”之说,但没有绝对的以区位来隔离诸夏与四夷。
在原始儒家那里,是否合乎“礼”是夷夏之别的关键。《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礼规定着天下秩序、国家规范、人伦准则,孔子在《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中以夷狄有无“礼”作为准则进行评判。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华”是“夷”主要以是否遵循“礼”作为标准,这一点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极为普遍。《论语·子罕》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君子居则化,非闭塞的蛮荒之域,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夷蛮之地的认可。处于诸侯争霸、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的社会环境下,孔子有此洞见与宽厚的心胸实属圣人之仁道。另一方面,孔子推进了自《诗经》《尚书》以来就形成的思想传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通过个体生命的“文”(礼)来化“天下”(文化世界),并试图以中庸之道把人的生命打开在宇宙整体中,从人性深处通达天道,削减诸夏、夷狄之区隔。
此外,在《中庸》“子路问强”一章中,孔子从南方之乐的彰显与赞叹中亦可印证孔子以文化而非地域、血缘来区分夷狄与诸夏的夷夏观。孔子所言南方是周代以来的江汉流域,相对于洛邑为中心的夷蛮之地,这里气候温润,聚居于此的族群在先圣舜、周公、召公等的礼乐教化之下形成中和之气禀,孔子谓之德性之强、君子之强。所谓“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是南方之强也”在孔子看来,风土不同,人之性情、审美亦不同,南方之乐“温柔居中,以养育之气”属于“君子之音”,北方之乐则“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此乃“小人之音”。通过南方之强与南方之音呈现了孔子的王道、德治之思,此二者构成了孔子夷夏观念的重要内涵。同时,在《中庸》中“强”与“柔”相融相荡,“强”者固执而中,是德性之强、君子之强,“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二十章)进一步强调了君子之学不为己,为则必要其成,百倍其功,择善固执,柔者可进于强。要言之,孔子从修身到治国安邦的思想在《中庸》中形成紧密的关联,从君子“慎独”到“劝学励志”到治国“九经”所蕴含的是君子个体“修身”意识介入到公共空间“群治”。孔子以中庸为至德,“柔远人”即为治国的一种实践智慧,在此过程中将忠恕之道(诚)施行于“他者”。也正是“柔”,作为一种不偏不倚的交往态度和顺四方,此为中庸之用也。
《中庸》篇末回到其根基问题——“至诚”,“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二十章)引文中“一者”即为“诚”,这里子思再次将“诚”“至诚”的本体论意义引入治国之道的阐释。如果没有“诚”的参与,治国“九经”只是虚文,可以看出,《中庸》对“哀公问政”的回答,从“政道”转向了“人道”。“人道”的内在逻辑王夫之鞭辟入里地阐释,合乎《中庸》旨意:“此人道二字,自仁义礼推之智仁勇,又推之好学力行知耻,而总之以一,一者诚也。此人道即后‘诚之者人之道也’,首尾原是一意。先虚言‘人道’而步步详求其实,只在‘择善固执’,‘己千己百’,皆人为之。人所以为道而敏政者在此。”其中,“诚”贯通了修身与治国之道,进而又勾连了“天道”,这是《中庸》的整体逻辑,第二十章文本则是对治天下国家始以修身的全面表述。在这一思路下,“柔远人”作为治国九经的方略,正是君子修身与治国之道的具体内容之一。一方面,通过反求诸己以“至诚”进而“敏政”,合内外以达道;另一方面,对他者身份、地位的承认,在上位不陵下,正己而行不求于他人,“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夷狄,行乎夷狄”。(《中庸》十四章)这一点与《论语》“言忠信,行笃敬,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相一致,修身乃是正己,正己的目的在于“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可以说,修身的最终目的在于治国,“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中庸》三十一章)从这个意义上,《中庸》的思路与孔子“修文德以怀远人”的主张一脉相承。儒家差序格局中,因有五伦,而有三事:家、国、天下。自我心性的完成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无限进程中,亦在对“他者”的观照践行中。
三、“柔远人”方略及现代意义
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往往体现在经典中,《中庸》在中国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并不是说它为中国文化给定了一个范畴与框架结构,而是打开了开放性的思维空间。《中庸》多被理解为儒家传续道统的经典,往往被加深了形而上的意义。但是,如果将《中庸》交付给政治哲学、人类学就不可避免地与“治国平天下”“夷夏之辨”等联系在一起,由此获得“道”与“器”的合一。《中庸》“九经”的阐述正体现了这一特征。“柔远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君子自身修养的开显,以“仁义”为核心采用安抚、怀柔之术对待作为“他者”的四方之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一举措所反映的是政治合法性有了“民意”的参与,因为四方之民的归顺是“平天下”的基础条件之一。但其前提在于君主能“以德抚远”,推行忠恕之道。对此,费孝通先生把传统社会以“己”推至“他者”的差序格局称之为“自我主义”,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但又不同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在费孝通看来儒家的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自我主义”具有相对性和伸缩性。“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只有自己,克己也就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里,我们无意评述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理论能否契合《中庸》“九经”中所涉及的九重关系。“差序格局”很好地为我们提供了以“群”与“己”、“公”与“私”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圈层结构。但是,基于《中庸》的解读,治国“九经”之间更像是平行的策略,以君主“修身”(仁义)为中心所展开的德治之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第十九章)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贤人、亲人、大臣、庶民、百工、远人、诸侯皆是治国平天下不能或缺的举措。
一定程度上,《中庸》“九经”代表了儒家德治主张及具体践行,对古代中国政治政策、民族政策、伦理原则诸多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留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印记,当然,当下的中国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汲取儒家文化中合理的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离不开当下社会的时代诉求与精神文化建构,在《中庸》“九经”中如果说君臣观念已经失去了思想基础,父子、夫妇的伦理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柔远人”可以说更贴近现代语境的转化。如上所述,“柔远人”所指向是的对华夏之外的“夷蛮”(四方之民)的安抚、怀柔。这是儒家夷夏观的集中表达,“远人”作为“他者”被纳入治国平天下的序列之中。这是君子“克己”的修身功夫介入到“群治”的公共空间方略之一,对“远人”的态度是“送往迎来,嘉善而不能”。(《中庸》十九章)朱子集注曰:“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对四方宾旅(少数民族)依据礼节对待,给予丰厚的赏赐接受菲薄的纳贡,这是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德治的推行,也是中庸所言“诚”的落实。“柔远人”作为君主施行仁政的表现之一,包含着先秦儒家对夷夏观念的基本态度,均在“天道”—“人道”—“政道”的逻辑系统中一以贯之。
儒家“柔远人”是中庸精神原则在“大一统”天下国家的具体践行,影响着历代王朝的政治选择与夷夏关系的张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民族国家,中庸之道仍影响着国家治理原则,遵循着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交往原则。这些原则表现在对“他者”文化、习俗、信仰诸多方面的尊重,在《原始人的心智》一书中,博厄斯运用实证材料有力地驳斥了白种人生来就在智力上高于其他人种的谬论。他认为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并非因为天生的智力水平造就,而是受历史条件与环境影响所致。因此,要了解特定地区的历史只能从该民族或地区的实际历史发展中获得。依据博厄斯文化相对论作为一个视角来审视“柔远人”何以可能,为“远人”及其文化找到恰当的理论工具。但是,博厄斯过分强调文化间的异质性,否认不同文化间存在普遍的规律性。这样必然带来一些困厄甚至卷入无法调和的逻辑矛盾。因为“柔远人”尽管凸显了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但也包含着儒家对夷蛮(“他者”)以德抚远的教化。教化意味着培育四方之民与中原有着共同的价值认同,对原始儒家而言,仁、义、礼、智即是人之为人的准则,这是教化的标准与目的。是否达到这一标准也是夷夏之分的依据。从博厄斯的角度来看,他反对依照唯一的理性辨准来了解别的文化和思想体系。因此,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文化相对论作为方法论仅仅供我们窥见一个侧面,它让我们看到并且承认每个民族拥有自身独立的文化和思想体系。中华民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塑造了56个民族灿烂的文化,构成了多元、多层次的中华民族文化。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历史动力,无论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概念对中华文明的传神描述,还是赵汀阳在《惠此中国》中论及的“中国漩涡”的解释模型,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与中华文明有着强大的兼容性不无关联。儒家思想则为中国文化确立自身找到了依据,并在“中庸”精神原则中打开了广阔的视域。“柔远人”作为治国“九经”方略之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儒学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不仅仅是经典的诠释,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它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中庸》“柔远人”的精神原则在治国理政中激发君子追求“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影响着历代王朝的夷夏观。“和合”思想亦在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过程中促进了各个民族的交流交往与交融,缔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和为贵”的精神特质与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复兴的当下,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以今人的眼光、时代的诉求与历史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柔远人”的精神原则也应该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进行新的阐释与转化,将中庸的实践智慧,注入新时期关注个体的善、社群的善、有益于中华民族共善的践行之中。
四、结语
孔子从修身到治国安邦的思想在《中庸》中形成紧密的关联,从君子“慎独”到“劝学励志”,再到治国“九经”所蕴含的是君子个体“修身”意识介入公共空间“群治”。孔子以中庸为至德,“柔远人”即为治国的一种实践智慧,在此过程中“柔”的态度与策略将忠恕之道(诚)施行于“他者”。从“柔远人”的注解中不难发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中,先秦儒家的民族观(夷夏观)隐含其中。“远人”的意涵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演进中,随着疆域的扩充而拓展,均是对自身与“他者”交往中的认知,并做出合乎中庸之道的行为选择与政治方略。
“柔远人”集中反映了儒家“他者”之道,一方面,通过反求诸己以“至诚”进而“敏政”,合内外以达道;另一方面,对“他者”身份、地位的承认,在上位不陵下,正己而行不求于他人。即作为方法论的柔远人表明君子修身的目的与践行,中庸之道在对“他者”的重视中得以彰显,从而塑造了中华文化“以和为贵”的特征。如果说“柔远人”是中庸精神原则在“大一统”天下国家的具体践行,影响着历代王朝的政治选择与夷夏关系的张弛,那么,作为儒家“他者”交往之道的“柔远人”它所彰显的是注重人的主体性及其群体的和谐。只有关注个体的善、各个民族的善,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善”。这既是儒家思想在现代语境下创造性转化并获得生命力的关键,也是中华民族在“和而不同”中发展壮大的关键。
(作者:杨晓薇,云南大理人,哲学博士,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儒学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
本文刊载于《伦理研究》(第九辑)第92-98页
上一篇 : 儒家“德行伦理”的道德评判原则及其现代意义
下一篇:创新“让德者有得”机制, 构建“好人有好报”的价值体系